《探秘苏东坡》| 官员东坡:翰林大学士
来源: 责任编辑:熊莉 2020年01月15 19:26:51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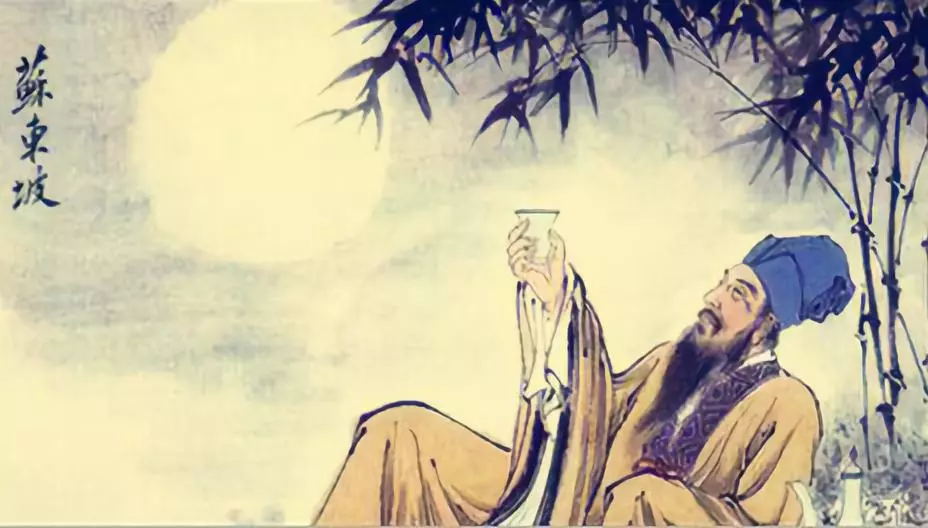
□文/刘寅
元丰八年(1085)四月,神宗逝,10岁的哲宗继位。高太后垂帘听政,复起一批旧臣,为首的是司马光与吕公著,苏轼也在其中。北宋奇人多,别看是朝廷官员,其实许多人都特色鲜明。就如司马光,他6岁时怒砸水缸,救下同伴,显示出异于常人的果敢。熙宁年间,他与王安石斗得你死我活,一怒之下返回洛阳独乐园,埋头写他的《资政通鉴》。这一去就是15年,期间他绝口不问国事,倒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史学名著。
有时候隐得越久,名声反而越大,当然这也和时势有关。神宗期间,全国百姓被新法搅得苦不堪言,人们无比怀念变法前那些平静的日子。当初痛斥新法的司马光,在百姓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。如今神宗走了,老百姓急盼着司马光出山,挽回局势。司马光成了人们的精神依托,所有的期盼都放在他身上,俨然如同“救星”一般。
同年夏天,司马光回京了。那一天,汴京城里比过节还热闹,全城百姓倾巢出动,争睹司马光的风采。从城门到朝廷,道路全被堵死,连着那屋檐上,老树的枝干上都爬满了人群。人们欢呼雀跃,喜极而泣,那场面,怕是如今所有的明星偶像凑一块儿也达不到。时年66岁的司马光,尚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,实在令人叹服。据说他例行去拜谒当朝宰相,百姓们不管不顾,竟爬到相府对面人家的屋顶上去。相府的卫士觉着不舒服,要赶,百姓却说:“我们又不看你家相公,只为看司马相公而已。”只苦了那相府对面的人家,得赔上许多银子去修缮被压坏的屋顶。
独居金陵的王安石得到消息,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司马十二做相矣。”他沉默一会儿,又往墙上大书“司马十二君子者也”,他的心情很复杂,甚至有些矛盾,但很贴切。司马光当然是正人君子,然而他主政后的政治理念也十分明确,便是要废尽熙宁新法,将王安石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。
再来看苏轼。自离黄州之后,一年多里,苏轼过得很舒坦,把江南一带的大好河山游了个遍。扬州、泗州、常州,他充分利用赴任的时间,一路悠着走,一点也不着急。官帽如飞,一顶比一顶来得高,但他如“小儿迂延避学”,能躲就躲。他两上辞官的状子,求朝廷准他买田归隐,生活东坡仍在延续,平静而自在的日子最是难得。奈何朝廷此时急需贤才,苏轼这样的人是跑不掉的。元丰八年六月,朝廷复起苏轼为著作郎,过了没多久,又命苏轼知登州军州事,官七品。朋友贺喜,他回言:“一夫进退何所道。”真的是兴趣不大,只可惜了江南山水,还有在常州宜兴买的几十亩田地,诗意栖居的蓝图又成了泡影。
但说归说,到了具体的位置上苏轼仍然兢兢业业。这是古代大文人为官共通的优秀品质,不论怀着何种情绪,总会依着心里的道德准则行事。他在登州(今山东蓬莱)仅待了5天,就为当地办了两件大事,包括整治水军,恢复民间食盐的自由贸易,刺激生产,百姓们拍手称快。今日蓬莱有苏公祠,上有对联云:“五日登州府,千载苏公祠。”
新的任命又来了:升苏轼为主管祭祀、贡举的礼部郎中。在登州床还没捂热,一家人又得上路。元丰八年冬,苏轼抵京。刚进京城,数千百姓即刻围了上来,人们喜迎东坡不在话下,并对他说:“请苏学士转告司马相公,望他不要离开朝廷,好好保重,我们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。”同为抵制变法的风口人物,百姓们希望苏轼与司马光形成合力,然而这事儿终究是很难说。司马光的性格苏轼很了解,人们称他温公,但外表温和,内心却是刚直如铁。他与王安石有些相似,都是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。苏轼的脾气大家也是清楚的,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,此番进京究竟如何?苏轼心里着实没底。
抵京不久,苏轼升起居舍人,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。官六品,是个很显赫的职位。三个月后,苏轼免试升为中书舍人,官四品,“被三品之服章”,兼翰林学士知制诰,负责起草诏令。短短四个多月,从七品小官跃升至四品高官,朝廷百官瞩目,而苏轼被搞得晕头转向。官升太快,难免遭人嫉恨,苏轼曾因此吃过大亏。他有些不安,上辞状称:“非才高、德重、雅望,不在此选。”但高太后不准,她是苏轼升官背后的主推手,新上任的两位大臣司马光、吕公著也共同举荐苏轼,一切在她看来是顺理成章的。高太后人称“女中尧舜”,她改年号为元祐,发起元祐更化,追慕仁宗朝嘉祐之治,苏轼自然是重要的一员。然而永远是世事难料,理想与现实的鸿沟,并非靠一颗虔心就能填补的。在纷乱的朝廷,命运如同狂风中的树叶,朝升暮坠。
元祐初年(1086),苏轼抵达他为官的最高点,更兼文坛领袖。自是富贵荣华,门庭若市,每日都热闹极了。然而这样的日子却不见得多享受,毕竟笼子再精贵,终究还是笼子,怎可与无边无际的大自然相比。苏轼写不出什么好诗词,倒是多了个饭后摸肚皮的动作。闲客附庸道:“先生满腹经文啊。”唯朝云笑说:“我看先生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呢。”苏轼听后哈哈大笑……
司马光此时已身居宰相,他累死累活,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,朝着贤人政治的方向努力。苏轼与他私交很好,一开始也合作愉快。有个插曲挺有意思。某日深夜,苏轼家里来了小偷。都说大官家里油水多,然而苏轼进钱快,散钱更快,他大多用来资助穷朋友了。偷儿摸了很久,却没甚钱财,墙上字画倒是能卖钱,奈何偷儿不认得。偷儿要开溜了,哪知苏轼已暗中盯他许久。门外下着大雨,苏轼对偷儿笑道:“墙边有伞,你拿了去吧。”偷儿吓坏了,拔腿就跑,一溜烟飞出了房檐。苏轼觉着有趣,第二天也和同僚们摆摆,然而几个官员面色凝重,憋了半天才笑出几声,大概是偷儿曾在他们家里得过手。
司马光听了,立刻拿此事大做文章,教导满朝官员要向苏轼学习,两袖清风,方能扶正社会的风气。熙宁年间,小人群起,官风败坏,道德沦丧,司马光极力想挽回。然而就如当年的王安石,司马光也走上了另一个极端。当指出这绝非公报私仇,而是司马光一贯坚持的政治理念。
我们说过苏轼是提倡渐变的,譬如病入膏肓之人,需先慢慢调理,不可一开始就灌猛药。司马光与王安石,两位铁腕宰相,两套极端的政策,苏轼一概反对,毫不让步。他与司马光的分歧逐渐公开化了。熙宁新法虽弊端甚多,但不乏一些成功的例子,比如保甲法、方田法。苏轼不同意尽废,理由是“法无新旧,以良为是。”宰相府里,司马光对在场的大臣们训话,偏苏轼要来插嘴。司马光很不高兴,丢下一句:“那你讲吧,我不讲。”调头回里屋去了。大臣们小声议论,苏轼自己被晾在那儿,憋了一肚子闷气,回家大喊:“司马牛!司马牛!”
安石牛,司马光也牛,苏轼被这两对牛角顶过来顶过去,很受伤。其实以他当时的条件,且不谈什么官场之术,单单把嘴闭上就能跻身宰相。然而中国古代大文人,哪一个不是心正性直,掏心窝子给众人看呢?苏轼如是,王安石、司马光也如是。司马光老了,进京之前就已抱病。他长时间劳累在案牍之上,终于顶不住了。元祐元年九月,拜相不到一年的司马光病逝。温公走前,写信给吕公著言:“光以身付医,以家事付子,唯国事未有所托,今以属公。”他是活活被累死的。而同年四月,王安石也逝于金陵,两人相隔仅五个月。



